陈寅恪之诗,除了叙述自己的境遇,显然是想勾起吴宓对往昔时光的回忆,并将这份温情投射到与陈心一破镜重圆的美好现实中。想不到吴宓前瞻后顾,左右摇摆了两年,与陈心一复婚之事仍无结果。因而,当他此次拜访陈寅恪夫妇即将离别的时候,唐筼专门让小彭把在广州的吴宓与陈心一所生长女吴学淑召到家中,与吴见面并共餐,以让吴宓真切感知儿女亲情,重温与发妻陈心一共度时光的旧梦。因吴宓已明确离广州后将重游北京并会见时在北京定居的陈心一,唐筼除了复劝吴抓住机会与原妻和好外,还敬重其事地赠陈心一方糖一包,强行让吴宓转赠。同时赠诗二首,其中末首为: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唐筼之诗,明确表达了期盼吴、陈复婚的良好祝愿。遗憾的是,吴宓北返,仍在合与分之间反复无常,终于无果而终。
9月4日晨,吴宓自中山大学招待所出发,乘车赶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陈寅恪诗中一句“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竟一语成谶。
9月6日晨,吴宓抵达北京。先后会见了贺麟、李赋宁、金岳霖、钱锺书、杨绛等昔日清华同事、弟子。贺麟对吴宓任教西南师院颇为惋惜,认为是虎落平川,难有容身和发挥才学之处,日后必然遭到犬欺。同时贺告诉吴一个消息,中共掌管宣传和文化的大员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住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贺麟欲陪导宓往谒周扬,宓惧祸,辞未往。惟此事而论,周扬实际上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据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所说,早年创办《学衡》时,曾翻译过英国小说家沙克雷的小说《钮康氏家传》(W。M。Thackeray
“The
Newcomes”),并在《学衡》连载,每期登一回。此为吴宓一生中最得意之译作,也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周扬当时应为关注者和好评者之一,因而几十年后产生了想调吴宓入京继续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想法。当贺麟对吴宓透露这一消息并欲拉吴顺杆往上爬时,已对政治有了警觉的吴宓没有响应,内中原因,许多年后吴宓在校订《自编年谱》时作了这样的解释“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纵观吴宓一生为人处事,憨厚有余而精明不足,结识的敌人与仇家自不必说,往往在许多时候被不怀好意的同事、朋友,甚至弟子引入早已挖好的坑中,上当受骗,落入无妄的屈辱与灾祸之中难以自拔。但这一次却是少有的异数,吴清醒而自尊地作了拒绝,在当时看来,这个抉择是明智的。至于日后于西师遭受的侮辱与肉体折磨,就不是吴宓的心智所能控制的了。
1961年9月13日早晨,吴宓在元配夫人陈心一住处检视从昆明运回、存放于此处的两箱书籍,作了妥善安排,准备离开北京。早餐时,吴宓面对陈心一贤慧的性格和殷勤伺候,想起陈寅恪夫妇、特别是唐筼再三让自己与陈氏复婚的殷切叮嘱,有些动情,但仍心神不定,无法下定决心剖白心事。联想到自己年已六十七岁高龄,陈心一也衰老了,此次分别,未必再能相见。想到此处,“忽觉悲从中来,几于食不下咽”。餐毕,吴宓在陈心一和友人陪同下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吴、陈这对恩怨夫妻就此永诀。
吴宓此次西行,除应陕西师范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还在妹妹吴须曼陪同下由西安返回家乡泾阳安吴堡探亲访友,此为吴宓离开安吴堡五十一年后首次返回故土,自是感慨良多。吴在安吴堡住一宿,于9月17日返西安,旋回重庆西南师院。此次重返,等待他的自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陷阱和地狱。
吴宓先是被内部监控使用,继之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受到一次次批判。到了1964年,吴宓原拟在暑假、十月上半、十二月下半请假再度南下,探望他一直挂念于心的陈寅恪夫妇,并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随着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犟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下半天动弹不得。
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惋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
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
妙笔生花所有文学作品均来自于互联网或用户供稿,如您发现侵权、违法、存在不和谐内容,请联系本站,我们将尽快进行删除处理! 客服邮箱:1308288070@qq.com
作者发布作品时,请遵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本站所收录作品、社区话题、书库评论均属其个人行为,不代表本站立场。
Copy 成都开外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渝ICP备19015976 版权问题处理联系:1308288070@qq.com
x章节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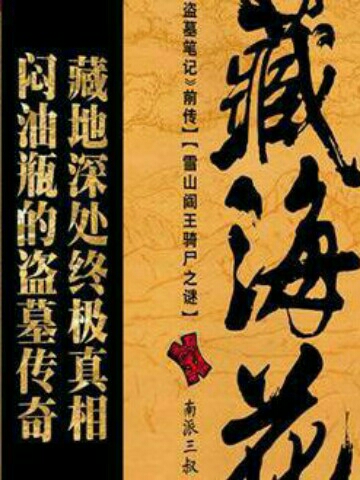 藏海花
藏海花 老九门
老九门 美人为馅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
诡灵道士